我根本不在意她的怒意,她沒有辦法。
誰讓陸家就剩聶聶一個獨苗苗了呢,陸夫人是不會放棄的。
她思索了一會兒。
「不如我們各退一步。」陸夫人提議,「我可以再給你三千五百萬,這筆錢足夠你優渥地過完這輩子了,而我只想知道我孫子的下落。」
事到如今,她還是認為錢能夠解決一切。
我把兩張黑卡都推回陸夫人的面前,搖了搖頭。
「看樣子你還沒有明白,錢對我來說已經沒有用處了。」
二十年前,我的確很需要很需要錢,為此不惜想要靠孩子得到錢。
可是我失敗了,孩子換不來我想要的。
並且我所擁有的也失去了。
我要錢有什麼用呢?
在陸夫人不解的注視下,我緩緩開口。
10.
爸爸的塵肺病已經很嚴重了,這個病沒得治。
他曾是我們家的頂樑柱。
長年累月地在工地操勞,飛揚的塵土深深侵入他的呼吸道,將這個絕症帶給他。
他修的是陸家投資的房產。
和他一起得了病的工友,沒有一個拿到工傷賠償。
上頭負責的人說,分明是他們自己身子弱,才得了病,現在還想來訛錢。
沒辦法,爸爸只好和其他得了病的工友一起去維權,卻被打了一頓,從此臥床不起。
迫不得已,媽媽只能靠環衛工那點微薄的薪資支撐起全家的生活。
有時候,媽媽還會去垃圾桶里撿些廢品賣,但她搶不過那些經驗老道的。
我想到爸爸牽著我的溫暖的手掌,媽媽輕撫我頭頂的模樣。
選擇了輟學去打工,我立誓,要賺很多很多的錢。
我曾經很渴望陸晟所說的那一千萬。
我知道爸爸的病是絕症,我查過,這個病很難很難,治不好。
但是如果有錢的話,可以用藥緩解。
我希望至少能讓他輕鬆一點,不那麼痛苦。
媽媽常年風雨無阻地在大街上清掃著,風雨侵入了她的身體,讓她的骨頭一降溫就會痛。
有了錢,我想讓她不那麼痛。
但是我沒能拿到一千萬,還多了個累贅。
我詰問著陸夫人:「要不要猜猜看,之後發生了什麼?」
「你少來!你們家倒霉,你不會是想說沒給你一千萬,所以你要把你家的倒霉算到我兒子頭上吧?」陸夫人尖厲地反駁。
我輕笑:「當然不是。」
爸爸媽媽很快去世了。
沒有錢,別說治療塵肺病了,連買點藥緩解都做不到。
我想買點止痛藥都不行,處方藥,貴,沒錢去醫院,開不出來。
最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陪在他身邊,看他的肺部一點點被灰塵侵蝕,看他漸漸地不能呼吸。
最後痛苦地窒息身亡。
禍不單行,媽媽在大街上掃地時被一輛飛速疾馳的機車撞飛,頭著地,當場沒了呼吸。
肇事者給的賠償讓我埋葬了父母。
「那輛機車就是陸晟的朋友開的。」我輕輕說,「看樣子陸晟的死,也沒攔住他們追求刺激的心。」
一千五百萬靜靜地躺在五星級餐廳高檔的楠木桌上。
「陸夫人你說,我還需要錢嗎?我想用錢留下的人,一個也不在了。」
「你以為用錢能買到一切嗎?如果可以,我希望爸爸媽媽能回到我身邊,你能買回我的爸媽嗎?」
「你做不到的。」
她臉上的血色轟然褪去,換之以無措的慘白。
陸夫人終於明白了,這世上總是有金錢所不能達成的目的。
她最喜歡的、最慣常用的、歷來所向披靡的法子,在我的面前失效了。
11.
她站起身,從包間的落地窗往外看。
從這裡能看見城市最繁華的街景。
聊得太久,夜晚已經降臨,高聳的地標性建築物亮起了它的霓虹。

3/3
陸夫人在窗前來回踱步,霓虹燈光映在她臉上,閃爍不停。
我靜靜地等著她的決定。
她又坐了下來,疲憊地說:「李香草,我承認你贏了。」
「我們陸家不能沒有一個繼承人,你的兒子是陸家的希望,所以我求你把他給我。」
陸夫人拋出了另一個誘惑:「難道你不想讓他認祖歸宗嗎?」
我指了指自己,「我不算他的祖宗嗎?」
陸夫人啞然。
沉默良久,她直直看著我的眼睛,眼神里沒有那股高傲了。
「你能給他好生活嗎?」
我摩挲了一下手上的老繭,感受著膝蓋傳來的微微刺痛,搖了搖頭。
陸夫人似是發現了機會:「難道你願意你兒子過和你一樣的苦日子嗎?」
「你知道我兒子,你也看見我另一個孫子,他們過得是什麼日子。」
她向後靠在座椅的軟背上,露出一抹拿捏住我的神色。
「讓你兒子回到陸家,我保證,他會從此過上富貴生活,榮華一生。」
我微微一笑:「你說的是,二十歲就早死的人生嗎?」
那可真是旁人艷羨不已的生活。
陸夫人已經被我刺的有些習慣了,她勸說我:「你不想你的孩子過上好日子嗎?不僅是他,你也可以過好日子。作為一個母親,你應該明白孩子的重要性。」
我搖搖頭,
孩子對母親是很重要,但是陸晟不配有孩子。
12.
「陸夫人,這些年我常常在想你為什麼說我的孩子是私生子。」
她沒忍住嘴角的一抹嘲諷:「你沒和我兒子結婚,生下的孩子自然是私生子。」
「我想你弄錯了。」我輕輕用勺子敲擊了一下茶杯,清脆的聲響讓我理清思路。
「我覺得,混淆私生子和非婚生子女概念的人,若是男性,必定是個想將女性吃干抹凈的惡虎;若是女性,必定是幫著惡虎的倀鬼。」
當年懷孕時,我十八歲,生下孩子,十九歲。
我國的法定婚齡是女性二十歲,男性二十二歲。
「照你的說法,在我國法定婚齡之下生出的孩子,都是私生子。所以我猜測一下,你口中所謂的家族聯姻,不過是辦了個婚禮,還沒領證對吧?」
我十分肯定,因為陸晟到死都沒有二十二歲。
「那又如何?先辦婚禮而已,若是我兒子還活著,肯定是要領證的,他們的孩子怎麼能算是私生子!」
陸夫人抖著嘴唇,「你自己下賤勾引我兒子,怎麼還敢拿你和、和我兒媳比較!」
我停下了敲擊茶杯的動作。
「我若是男子,便日日去尋二十歲以下的女子,總能禍害幾個留些孩子出來。」
積攢了二十年的痛苦在這一刻噴薄而出。
我怨毒至極的話語狠狠地砸向陸夫人。
「什麼你的孫子,我的兒子,從來沒有過這種東西。」
我站起身,平生第一次俯視別人惡意地說:「或許你可以尊稱他一聲『奸生子』。」
聶聶的聶,實際上是孽種的孽。
陸夫人震驚不已地看著我,惶惑在她的臉上暴露無遺。
我心中快意至極。
等了二十年,我終於等到了這一天。
13.
二十年前,我認識陸晟便是在我工作的 KTV。
按理說,以陸晟的身份不應該來這種不高檔的地方。
但他的朋友們哄著他來了。
一群人在包間裡不知道玩鬧什麼。
老闆讓我給裡面再送一盤水果,我乖乖地去了。
裡面人太多了,陸晟不知道怎麼倒在地上,臉上緋紅不已。
我小心一一地想要繞過他,把水果盤放在桌子上,卻還是不小心碰到了。
他一把把我拽到,雙手在我身上亂摸。
旁邊所有人都在起鬨。
我驚慌失措地呼救著,可包間是隔音的。
那是我永生難忘的一天,在眾目睽睽之下,陸晟占有了我。
清醒後,他只是隨意地朝我擺擺手,絲毫沒有愧疚。
而我來不及多想,穿起衣服慌忙地逃出包間。
我想向老闆提出辭職,可那天剛好發工資,看著手裡的鈔票,我知道我不能失去這份工作。
陸晟知道自己被朋友們算計了,只是笑著安撫朋友:「你聽她的名字,就是個命賤的草而已,慌什麼。」
可我不命賤,我的名字是爸爸翻著字典取的。
盼我如草般堅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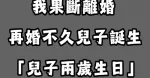
 武巧輝 • 2K次觀看
武巧輝 • 2K次觀看
 楓葉飛 • 1K次觀看
楓葉飛 • 1K次觀看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