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警察阿姨,我不是故意開門的,可他們吵架,我真的好害怕,我怕爸爸打媽媽,也怕爸爸要把我丟掉,我只是想著,爸爸不在家就好了,他不在家的時候,媽媽不會哭,外婆也不會不說話......」
六歲的孩子,帶著委屈的哭腔,這樣說著。
而備受矚目的江琴。
如喪考妣,呆坐在房間裡。
警察問她為什麼織毛衣。
過了許久,她終於捂著臉,眼淚從指縫裡噴涌而出。
「戀愛時他最喜歡我給他織的圍巾,我想再給他織一條,挽回我們的婚姻......」
「貝貝還小,我只是想讓她在完整的家庭里長大......」
明明一切疑點重重,明明公安測試了一萬種方案,幾乎每一種李懷勤都有生還的可能。
可偏偏,就如同被閻王點卯一般,李懷勤踩中了每一個巧合,成就了這場意外。
無數記者蹲守在公安局門口,等待一個答案。
就在這時,一枚炸彈引爆了所有輿論。
有人放出一段視頻,視頻里,我站在小區樓下,拿著垃圾袋和李懷勤爭執不休。
身旁,還站著幾個正在看熱鬧的老頭老太太。
然後下一秒,我猛地伸出手,給了李懷勤一巴掌。
他的框架眼鏡被狠狠甩在地上,碎成兩半。
評論區頓時炸了。
【這人又是誰?為什麼會給李懷勤一耳光?!】
【我靠我知道她是誰,這就是那個見死不救的鄰居!】
【狗頭保命啊家人們,我也住這小區,他們吵架我聽到了,好像是男的把用過的計生用品塞鄰居垃圾袋裡,小區大爺大媽都傳說那個女鄰居是賣 Y 的......】
【樓上真的假的?如果是真的,那這男的也是賤沒邊了!】
10
警察很快敲響了我家房門。
依舊是那位眼熟的女警察。
這一次,她看我的目光更加銳利。
「上次問詢的時候,你為什麼不說你和李懷勤前一天剛起了衝突?」
「我以為這對案件沒什麼影響。」
「江琴的母親,曾經是你的老師?」
我不置可否的點了點頭。
江琴的母親,曾作為優秀教師代表,在退休後去監獄任職教育改造。
但她和其他那些帶著有色眼鏡的老師不一樣。
她溫和,善良,自學了心理干預和疏導,對我們這些年紀偏小的犯人做潤物細無聲的心理安慰。
她教了我三年。
直到那天,她拿著一家四口的照片給我看,說她女兒馬上就要生了,她很快就要去照顧外孫女,不能再來監獄授課了。
也是那天,我看到了照片里,坐在年輕的,懷孕女孩身邊的,那個我此生都不會忘記的男人。
是李懷勤。
那一瞬間,我渾身雞皮疙瘩乍起。
他就像陰溝里的蟲子,好像不在,又好像無處不在。
我點了點那張英俊的臉。
「他,對您女兒好嗎?」
江琴母親笑著說,很好。
她說那是個很善良的男孩子,雖然家庭條件差了些,但自身很努力,也配的上她女兒。
直到一年前,我出獄。
在小區樓下再次偶遇了老師。
她變化很大,背包里腫瘤醫院的片子支楞出一個角。
原本很顯年輕的臉龐爬滿了皺紋,頭髮全花白了,眼底也晦暗無光。
我們攀談著,進了同一個單元樓,同一部電梯,最後停在同一樓層。
真是機緣巧合,我和老師一家成了鄰居。
夜裡,我聽到隔壁傳來吵架的聲音。
然後是皮帶抽過身體的悶響。
女人似乎被捂著嘴尖叫,那聲音在夜裡像是鬼哭。
第二天又遇到老師,我問了她幾年前我問過的問題。
「他,對您女兒好嗎?」
這次,她沒有回答。
警察審視的看我,然後徑直推開門,走進了我的臥室。
「你貼的那些隔音海綿呢?!」
我淡聲:
「隔壁都沒人住了,我也不需要隔音海綿了,都拆了。」
女警察目光炯炯。
「我們調查過了,雞蛋棉本身是吸音棉,而非隔音,你之前那樣貼,只會讓凹凸面把你自己的聲音反射回去。」
「你根本沒有防住隔壁的聲音,反而......」
「是隔絕了隔壁聽到你的聲音!」
我看著她,「那又能說明什麼呢?除了說明我是個吸音、隔音傻傻分不清楚的人以外,什麼也證明不了?」
「不!」
「這就證明,那天晚上,你一定聽到了什麼!」
講真的,警察這套翻來覆去的問詢,我真的已經煩了。
「該講的,我都講過了。」
「我能聽到什麼呢?聽到李懷勤又在毆打他的妻子,並在期間逼迫女兒不停的彈奏鋼琴掩蓋,然後讓老師目睹自己的女兒和孫女兒受折磨?」
「這又能說明什麼呢?這也不能說明老師就是故意殺人,這只能說明李懷勤該死!」
我收攏情緒,長舒口氣。
「您還有什麼想問的嗎?」
「如果沒有的話,那您請回吧,我已經耽誤了好幾天,現在要去工作了。」
女警察帶著疑惑離開。
很快,李懷勤案件宣判。
江琴母親被判過失傷人,判處五年有期徒刑,但因身體緣故,緩刑兩年執行。
當年,江琴給自己母親出具了諒解書,並申請了保外就醫。
新年夜,江琴做了一桌飯,貝貝端來飲料,老師靠在沙發上,眉眼溫和含笑。
這時,門鈴響了。
女警察眸光銳利,掃視全屋。
「陳珂呢?」
「陳珂在哪?!」
11
我在轉機途中接到了警察的電話。
對方聲音急切,帶著粗重喘息。
「我知道了!我知道你為什麼一定要讓李懷勤死了!」
「陳珂,不,我應該叫你陳書。」
「當年你和李懷勤網戀,卻沒想到李懷勤為了江琴要拋棄你,你一怒之下舉報了他,還在他們學校論壇放出五十幾頁的 PDF 控訴他,不是嗎!」
我忍不住輕笑出聲。
「警官小姐,您到底想要說什麼?」
「是你故意打碎李懷勤的眼鏡,迫使他當天不得不佩戴隱形眼鏡出門!」
「李懷勤有嚴重的乾眼症,深夜回家時眼球乾澀難耐,再加上江琴拿著小三 B 超故意找茬,他們才爆發的爭吵。」
「李懷勤又想動手,江琴母親早就恨極了李懷勤家暴還轉移走了江家的全部財產。於是假裝踩到玩具滑倒,把硫酸潑到李懷勤的臉上。」
「誰會好端端的,在沙發上放著毛衣針!偏偏那天晚上,江琴的圍巾織到一半,就放在沙發上!」
「而當李懷勤向你求助時,你明明全都聽到了,但你放任他去死。」
「陳書,這就是你的報復,不是嗎?」
我忍不住要為她鼓掌。
和陳珂互換名字這許多年,以至於警察喚我陳書時,我還會怔愣幾秒才能回神。
是。
九年前,我是陳書。
自從三年級我在奧賽上嶄露頭角後,我媽便將生活的大半重心全都轉移到我身上。
那年我還是不過九歲的孩子,我媽卻壓著我,逼我提前去學完初中和高中的課本。
她深信不疑,認為我是老陳家百年難得一見的天才,是能帶著她和我爸從這個爛泥一樣的生活中飛出去的鳳凰。
這也導致,她幾乎 24 小時,監控我生活中的一切。
為了區分我和陳珂,她強逼著陳珂剪了假小子一樣的短髮。
然後就死死守著我。
即便那些題目課本她看也看不懂,卻要逼著我每天學夠至少 16 個小時。
睡覺的時候,她守著我睡。
學習的時候,她守著我學。
甚至上廁所的時候,她都在門口掐著表。
哪怕一次意外失分,我害怕得躲在學校廁所不敢回家,我媽卻直接衝進教學樓,大呼小叫,喊我的名字。
那天我躲在廁所,雙手捂著耳朵,緊閉雙眼,只希望自己能忽然從這個世界消失。
當晚,我寫卷子寫到凌晨四點。
我媽手拿戒尺,靜悄悄、直勾勾的死盯著我,直到我寫完最後一個字。
我和陳珂,就像蹺蹺板的兩端。
一邊給的太多,一邊又給的太少。
兩端都不滿,兩端都難過,最後愈演愈烈,蹺蹺板巋然崩塌。
高三那年,學校換了新教導主任,給所有女生都剃了高三頭。
有同學笑著打趣。
「原本還能用長發短髮區分你和陳珂,現在可好了,根本傻傻分不清楚。」
那一天,我看向陳珂,恰好她也看向我。
我們開始第一次互換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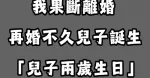
 武巧輝 • 3K次觀看
武巧輝 • 3K次觀看
 楓葉飛 • 2K次觀看
楓葉飛 • 2K次觀看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