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自從我搬回老屋起,便總能聽到這對夫妻壓抑到嗓子眼的低吵。
起初是女人看孩子大了想要出去找工作。
「李懷勤,你之前答應了我的!只要等貝貝去上了幼兒園我就可以繼續去工作了!」
「李懷勤!我們說好了的,不論男女,就只要貝貝這一個孩子!」
「李懷勤,你的銀行帳戶為什麼凍結了?房貸催繳電Ṱúⁱ話都打到我這來了!你是想讓我死嗎?!」
漸漸的,女人的聲音從壓抑到嘶吼。
背景音里,只有小女孩彈琴的聲音,嗚咽著彈錯了一個又一個音調,緊跟著便是男人摔摔打打的聲音。
「這他媽就是個弱智!學了一年了,連一首最基礎的曲子都沒辦法連著彈下來。」
「你不生,你是要我老李家徹底斷送在你手裡嗎?!」
「我告訴你江琴!你一天不生二胎,就一天別想花我老李家的錢!」
吵到最後,便是女人哀哀低低的哭泣,和男人摔門而去的巨響。
他們吵架吵得很兇,又頻繁,因此我才在臥室牆壁上貼滿了雞蛋棉。
可即便如此,某些聲音依舊可以透過大門縫隙鑽進我的耳朵。
比方說——
半年前,隔壁男人出軌了。
趁著女人送孩子上鋼琴課的下午,老太太出門買菜的間隙,隔壁那位衣冠楚楚的大學教授先生,帶著一名年輕女孩回了家。
一牆之隔,我清清楚楚地聽見男人的低喘,以及那女孩聲聲喚著:
「老師。」
「老師。」
自那之後,隔壁夫妻夜間的爭吵變得更加兇猛,最後從摔摔打打升級到骨頭捶過皮肉的尖叫和悶響。
那也是第一次,我從小區物業群里添加了隔壁女人的聯繫方式。
【您好,我是 1702,請問您需要幫助嗎?】
次日,那位長相酷似山口百惠的女人敲響了我家房門。
盛夏酷暑,她一身高領長裙的日式好嫁風穿搭。
把一盤洗得乾淨清透的葡萄端到我面前來。
「不好意思哈,我女兒早晚總是練琴,彈得不好,打擾到您了吧?」
小女孩就怯怯地貼著她腿邊站著,見我看過去,她忽地抱緊了女人的大腿。
女人低低嘶了聲。
又很快噤聲。
我接過葡萄,露出我掛在脖頸的降噪耳機,遞給小女孩一根棒棒糖,三言兩語維護了女人的臉面。
「不會,我晚上習慣戴著降噪耳機睡覺,什麼都聽不到。」
「所以你的意思是,李懷勤......」警察忽然打斷了我的敘述,「經常家暴他妻子,是嗎?」
她表情太過嚴肅,我忽然也就有點兒納悶。
「上個月,隔壁也報過警,當時警察怎麼說的來著?」
那天李懷勤與江琴吵得極凶。
我聽出,是李懷勤在外面的小三懷了孩子,發 B 超照向江琴逼宮。
「李懷勤!你這樣對我和貝貝,你還算是個人嗎?!」
是買菜回來的隔壁老太太報的警。
可警察剛敲開門,李懷勤便率先走出來,攬住江琴的肩膀,笑著對警察說:
「不好意思,就是尋常夫妻吵架。」
「你們瞧瞧,把我臉都抓花了,該報警的是我才對吧。」
說著,他寵溺地揉了揉江琴的頭,女人臉頰上甚至還帶著一塊明顯的淤青。
但在那一刻,所有人都選擇視而不見。
警察語氣平靜,公事公辦:「要不要立案?立案就先去醫院驗傷,不去就在這簽字,下次這種家長里短自己解決,不要隨便報警浪費警力。」
李懷勤一手攬著江琴。
另一手死死抓著年幼的女兒。
女兒發出痛呼。
老太太捏緊了手裡的菜籃,露出滿頭白髮。
最後江琴妥協了。
她垂下頭,在紙上籤下了自己的名字,表情難看至極。
我困惑地看向警察。
「當時不是你們說,別隨便報警浪費警力嗎?」
「你們說隔壁死人了,到底是誰死了?又是怎麼死的?」
「我不過是個無辜的鄰居,你們一直盤問我做什麼?」
這時,那名警官卻忽然反問:
「陳珂,你知道死的是誰嗎?」
奇怪,我怎麼會知道?
照片里那人,臉皮都詭異地全部爛掉了。
一雙眼眶黑咕隆咚,連眼球都沒有,後腦勺也是憋進去的。
更不要說身上的襯衫了,全是血漬和不知什麼污漬,恐怕親媽來了都認不出,更何況我這麼個八竿子打不著的鄰居。
女警察直勾勾地看著我,眼神冷厲。
「昨晚死亡的,是李懷勤。」
「根據江琴的證詞,是江琴母親昨晚用硫酸刷廁所時,李懷勤忽然回家,夫妻間爆發了劇烈爭吵,老人被嚇得手抖,硫酸被不小心潑到了他臉上,他戴的隱形眼鏡被溶解後,發瘋似的在屋內亂跑,脖子撞上了江琴的毛衣針。」
「更巧合的是,李懷勤當時失血過多,想要求救,他年僅六歲的女兒卻害怕地打開了房門。」
「陳珂,你家大門上,還有李懷勤的手印。」
「他昨晚敲過你家房門,無果後他想要從電梯離開,卻不知為何走到了樓道紗窗邊,最後失足從十七層跌了下去。」
警察一錯不錯地盯著我,連聲質問。
「是一系列的巧合,造成了李懷勤的死亡。」
「但是陳珂,昨晚李懷勤的求救,你真的沒有聽到嗎?」
「還是因為他之前的所作所為,你故意選擇不幫他?!」
我眼瞳震顫,寒意從背後升起。
「這些巧合,真的都是巧合嗎?!」
4
李懷勤人長得蠻斯文。
戴著一副金邊眼鏡,在附近一所大學當法學老師。
因為十八歲那年的意外,我對與異性接觸產生了十足的厭惡和牴觸情緒。
但李懷勤是個很懂得分寸的男人。
因為身份問題,我對工作需要比常人付出更多努力。
這也導致,我經常過著海外時間,飯吃得不準時準點,垃圾也時常忘記丟。
有好幾次,都是我把垃圾放在門口,再反鎖了大門後,隔壁房門便悄然打開,然後我的垃圾袋就也一起消失不見了。
警察用審視的眼光看我。
我闔了闔眼,深吸口氣,繼續說。
起初,我也以為李懷勤是好心。
以為他人如其名,虛懷若谷,勤勞善良。
但並不是。
他將偷情後的個人物品全部塞進我的垃圾袋裡。
大到各種花活用品。
小到被撕成碎片的絲襪和用過的套子。
我們小區的每個垃圾桶,幾乎都 24 小時守著幾個老頭老太太,幾乎垃圾剛被丟進垃圾桶,那些不知分寸且大嘴巴的老人就會蜂擁而上,當著你的面撕開垃圾袋,並在裡面挑挑揀揀。
水瓶和紙箱?留下。
用過的套子,他們便互相交換一個戲謔的眼神,留作茶餘飯後的談資。
不過半年,小區里關於我的流言蜚語已經漫天遍地。
很偶爾的幾次下樓,都有人對著我的背影指指點點。
後來不知怎的,有人扒出我曾入獄多年。
「白天都拉著窗簾的,晚上燈卻要亮一整晚的嘍。」
然後輿論導向便漸漸變得不可控制,造謠我當初因為聚眾 Y 亂被警察抓進去坐牢,更不要說,還有垃圾袋裡大量使用過的計生用品作為審判我的證據。
我為此苦惱不堪。
出獄後,我一直過著深居簡出的生活,但因為李懷勤的舉動,又讓小區那些八卦的視線全都落在了我身上。
這無疑不又讓我想起那年,面對無數記者的話筒,我姐僵硬著臉被父母摟在懷裡,而他們面對記者關於我的提問時,卻鄙夷又厭棄地開口:
「陳珂從小就不是個好東西,打架鬥狠,嫉妒姐姐,腦袋比豬圈裡的豬還要愚蠢!」
「她早就該被送進監獄裡好好改造改造!」
「要不是她非鬧著讓她姐姐回來的路上給她買什么小蛋糕,她姐姐怎麼可能會從那條小巷子走?又怎麼可能會遇上這種事?」
我媽對著鏡頭嚎啕大哭。
「她就是個害人精!就怪她天天和那些混混廝混在一起!」
「我的書書,我的書書應該有光明的未來,都讓她給毀了!」
彼時我姐作為受到侵害的區文科狀元,備受社會矚目,而我媽的話,毫無意外地讓所有人將厭惡的目光投射到我身上。
甚至有人惡意揣測,是否我因嫉恨姐姐聰明,引導壞人共同出演這樣一出大戲。
閃光燈聚集。
如芒刺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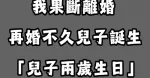
 武巧輝 • 3K次觀看
武巧輝 • 3K次觀看
 楓葉飛 • 2K次觀看
楓葉飛 • 2K次觀看




















